吴 歌
在汉语诗歌的星空中,总有一些特立独行的星辰,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发光发热。诗人默默及其开创的撒娇诗派,便是这样一群奇迹般的存在。2025年4月24日,默默的《重新识字》百部系列诗集面世庆祝会在上海科学会堂隆重举行,这不仅是诗人个人创作生涯的里程碑,更是当代汉语诗歌一次重要的文化事件。从“撒娇诗派”到“重新识字”,默默以其独特的诗学实践,完成了一次对汉语诗性的深度挖掘与重构。
一、默默其人其文:在汉字迷宫中的探险家
默默是一位语言的炼金术士,更是一位在汉字迷宫中不懈探索的冒险家。杨四平教授在庆祝会上指出,默默延续了从仓颉到许慎的传统,重新建构汉语语义,对汉字中蕴含的文化密码进行解密。这种评价绝非过誉——默默的诗歌创作确实呈现出一种对汉字本质的执着探索。
在《默默同音字新作:爱》中,诗人以惊人的语言敏感度,将“爱”与“癌”通过音近关系串联起来,形成了一种令人震撼的诗意效果:“我们的爱会让我们得癌/我们的挚爱哪怕她只爱我们也更会让我们致癌”。这种看似荒诞的联想,实则揭示了爱作为一种强烈情感的毁灭性力量。默默通过同音字的游戏,解构了传统关于爱的浪漫想象,呈现了爱的复杂性与危险性。这种文字游戏不是简单的语言技巧展示,而是对汉字本质的深度挖掘——在汉语中,音同或音近的字往往在意义上也存在某种隐秘联系,默默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联系,并将其转化为诗意的表达。
谢建文教授认为默默的诗歌逻辑清晰,有着强烈的对艺术形式的在乎,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彼得·汉德克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点在《写在十字架上的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诗人以年龄为线索,从十岁写到九十岁,每个阶段都以“十”或音近字为联结点:“十岁的时候自己是谁还不清楚/十一岁就感到人生失意这孩子一定是个小老头”。这种结构既有着清晰的逻辑框架,又在这个框架中充满了语言的跳跃与联想,形成了一种严谨与自由并存的特有诗风。
白夜注意到默默在诗歌创作中不同于北岛喜欢运用意象,而是以白描和排比的手法,延续了《诗经》中一唱三叹的传统。这一点在默默的诗作中确实十分明显。他的诗歌往往避免使用晦涩的意象,而是直接运用语言本身的力量,通过重复、排比、音韵等手法,创造出强烈的节奏感和音乐性。这种创作方式使得他的诗歌既具有现代感,又有着深厚的传统根基。

左起:吴歌 李亚伟 孔祥仁 默默 颜飞 边八哥
二、默默与撒娇诗院:诗意栖居的乌托邦
撒娇诗院不仅仅是默默和诗友们活动的场所,更是一个精神的家园,一个诗意栖居的乌托邦。从1985年第一届撒娇诗歌朗诵会开始,到2023年的各类诗歌活动,撒娇诗院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个重要据点。
杨四平教授在《我也要撒娇》一文中生动地描述了撒娇诗院的氛围:“在撒娇诗院,我几乎把我以前的这些想法都要抛弃了。因为我的皓首穷经其实存在很严重的生命浪费。”这种感受揭示出撒娇诗院的独特价值——它不是传统的学术机构,而是一个充满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空间。在这里,诗歌不是被研究的对象,而是生活的方式。
撒娇诗院的活动记录令人印象深刻:从京不特、芒克、严力等知名诗人的朗诵会,到各种主题的诗歌研讨会;从上海到香格里拉,再到西双版纳,撒娇诗院的活动地域不断扩展;从传统的诗歌朗诵到诗画展、研讨会等多种形式,撒娇诗院创造了丰富多样的诗歌活动模式。这种持续而多元的诗歌实践,在中国当代诗歌界是十分罕见的。
郭吟在《撒娇诗学》中阐述了“撒娇”的诗学理念:“‘撒娇’是卖乖?掩人耳目而已,实则是捣蛋,是戏谑,是无拘无束的嘲讽和不露声色的表达,更是呈现破碎了的精神游戏。它的显著特征却是严肃。”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正是撒娇诗派的精髓所在——以轻松甚至戏谑的方式表达严肃的思考和精神追求。
默默作为撒娇诗院的院长,无疑是这个诗意乌托邦的灵魂人物。张露提到,默默是非常勤勉的写作者,日常工作和创作达到十个小时。这种勤奋不仅是个人创作的需要,也是维系和发展撒娇诗院这个诗歌共同体的基础。默默不仅自己创作,还组织活动、提携后人、促进交流,为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默默百部诗集的贡献:汉语诗性的重新发现
默默的百部系列诗集在汉语诗歌写作历史上具有空前规模和文化意义。这些诗集不仅仅是数量的积累,更是对汉语诗性一次系统而深入的探索。
杨四平教授将默默的写作与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都是对汉语的重新发现和建构。默默的《默默同音字字典》确实与《马桥词典》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通过语言的地方性、历史性和多义性,探索汉语的丰富内涵和文化密码。不同的是,默默是以诗歌而非小说的形式进行这种探索,这使得他的作品更加直接地触及语言本身的诗性。
默默的百部诗集对汉语诗歌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拓展了汉语诗歌的语言边界。通过同音字、谐音等手法的运用,默默挖掘了汉语音韵系统中的诗意潜力。在汉语中,音同或音近的字往往在意义上也有联系,这种联系为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默默敏锐地捕捉到这种可能性,并将其发展为独特的诗学策略。
其次,他连接了传统与现代。默默的诗歌既有现代诗歌的实验性和先锋性,又有着深厚的传统根基。白夜指出,默默以白描和排比的手法,延续了《诗经》中一唱三叹的传统。这种连接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对传统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再次,他打破了诗歌与生活的界限。默默的诗歌往往从日常生活出发,但又不止于日常经验,而是通过对语言的锤炼和重塑,达到对生活经验的升华和超越。吴驾注意到默默延续了中国传统诗歌的脉络,从《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默默的写作保有了优秀的传统表达形式。这种传承不是形式上的模仿,而是精神上的延续。
最后,他创造了个人与历史的对话。默默的诗歌既是个体经验的表达,又是对历史和文化的反思。在《写在十字架上的诗》中,诗人通过个人生命历程的叙述,折射出时代和社会的变迁。这种个人与历史的对话,使得他的诗歌既有私密性,又有历史感。

2025年3月云南诗歌诗评家吴歌视察撒娇诗院
四、品默默及其撒娇诗友诗文:多元声音的合唱
默默的诗歌成就离不开撒娇诗派这个群体的影响和支持。在庆祝会上,多位诗人学者对默默及其诗友的作品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呈现出这个群体多元而丰富的声音。
谢建文的《北风之北》展示了一种深沉而辽阔的诗意:“我从渐次温暖的南方以尽可能温暖的诗行望着你/不能想象你是一眼泉或一汪湖水/你是无涯的浮冰辉耀无边的太阳”。这首诗以北方为意象,表达了对遥远、寒冷而纯洁的向往,语言简洁而意境深远。
喜然的《芭蕉》则呈现出一种柔韧而坚韧的力量:“它的领地,写满了放弃。以至于放弃几乎是她唯一的坚持/从打破自己开始她也打破了人们对于草本固有的迷信”。诗人通过对芭蕉的描写,表达了一种不同于常规的生命哲学——通过放弃而获得,通过打破而建立。
吴驾的《楝花开了》以细腻的观察和冷静的笔调,描绘了城市中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景:“楝花按时开了我从地铁出来,机械地走到制造局路/苦楝树下,过往的人不多/烟纸店的老板坐在门口/挂钟停在墙上”。这首诗通过对细节的捕捉,呈现了现代都市生活中的诗意瞬间。
陈行的《老爸的宅子》以简洁而略带讽刺的语言,揭示了财富和家庭关系的复杂性:“老爸发财后买下好多宅子/一座四合院让爷爷奶奶养老/一幢别墅由我和爸妈以及金毛住着”。这首诗看似平淡,实则通过宅子的分配,暗示了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和情感距离。
张露的《我跟未来打了一个电话》以重复的“你听懂了吗?”为 refrain,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节奏感和质问语气:“神圣的国家利益不要去触碰你听懂了吗?/联系到未来我与未来通了一个电话你听懂了吗?”这首诗通过对当下与未来、现实与理想的思考,表达了一种困惑和质疑。
这些作品风格各异,但都体现出撒娇诗派的一些共同特点:对语言的敏感和实验,对现实的关注和反思,对传统的尊重和创新。这些多元的声音构成了撒娇诗派丰富的合唱,也为默默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语境和对话者。
五、撒娇诗之未来:在传统与创新之间
展望撒娇诗派的未来,我们既可以看到挑战,也可以看到机遇。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时代,诗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撒娇诗派如何在这种变革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发展方向,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首先,撒娇诗派需要继续深化对汉语特质的探索。汉语作为一种表意文字,有着独特的音形义关系,这为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默默和他的同人们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探索,但仍有许多未知领域等待开拓。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保持汉语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同时又能与其他语言和文化进行对话,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其次,撒娇诗派需要进一步拓展诗歌的传播方式和受众范围。在数字化时代,诗歌不再局限于纸质出版物,而是可以通过网络、社交媒体、音频、视频等多种渠道传播。撒娇诗派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新媒体,让诗歌触及更广泛的受众。同时,也可以通过多种艺术形式的交叉融合,如诗歌与音乐、绘画、戏剧等的结合,创造更加丰富多元的艺术体验。
再次,撒娇诗派需要加强代际传承和人才培养。默默作为撒娇诗派的领军人物,已经为中国当代诗歌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一个流派的持续发展需要新生力量的不断加入。撒娇诗院可以通过工作坊、研讨会、奖学金等方式,培养年轻诗人,确保撒娇诗派的活力和延续性。
最后,撒娇诗派需要在保持独特性的同时,加强与其他诗歌流派和文化的对话交流。撒娇诗派以其独特的“撒娇”姿态和语言实验,在中国当代诗坛独树一帜,但这种独特性不应导致封闭和排外。相反,通过与其他流派和文化的对话,撒娇诗派可以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诗学理念和实践。
默默在庆祝会上强调:“汉语写作者最终落脚点还是回归到汉字,运用传统文化的,以东方式的母语写作。”这句话不仅总结了默默的创作理念,也指出了撒娇诗派未来的发展方向——在深入挖掘汉语特质和传统文化的同时,保持开放和创新态度,创造既有民族特色又具有世界意义的诗歌。
结语
默默的百部诗集不仅是个人创作的里程碑,也是中国当代诗歌的重要成就。通过对汉语特质的深入探索和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默默开辟了一条独特的诗歌道路。撒娇诗派以其独特的诗学理念和创作实践,为中国当代诗歌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传统与创新、个人与历史的张力中,默默和他的同仁们继续着他们的诗歌探险。他们的创作告诉我们,诗歌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态度——在看似“撒娇”的轻松姿态下,是对语言、文化和生命的严肃思考和探索。
默默撒娇诗不默默不撒娇——这个看似矛盾的标题,恰恰捕捉了默默及其诗歌的精髓:在表面的低调和戏谑下,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存在和严肃的精神追求。这正是默默和他的百部诗集给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
2025年8月,于景洪市第四中学书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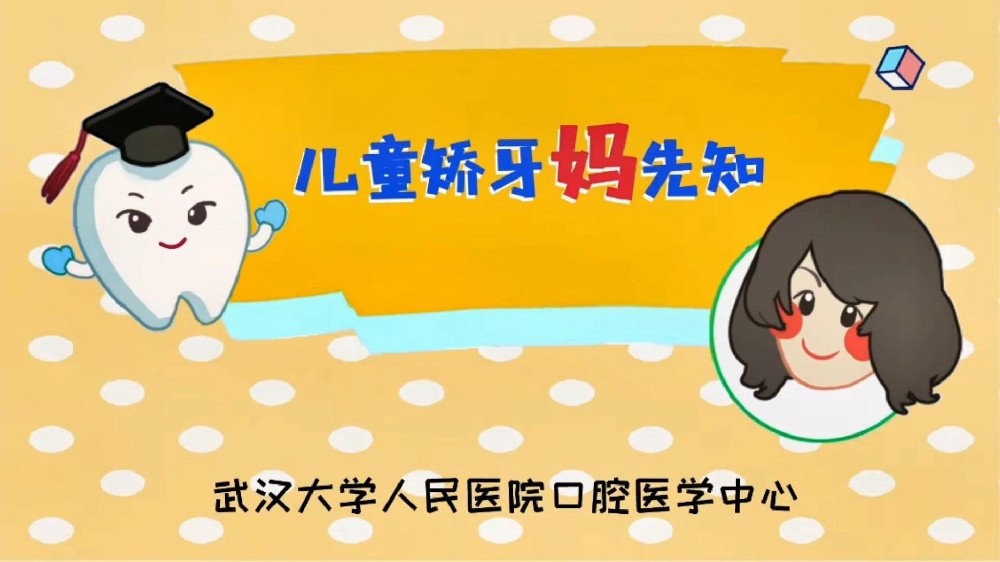





 丨中国财经新闻在线诚信合规举报 |
丨中国财经新闻在线诚信合规举报 |